人物生平
严耕望于194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师从于历史学家钱穆。
历任齐鲁大学研究所助理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人、耶鲁大学客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讲座、东吴大学特约讲座、新亚研究所教授。1970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中古政治制度及历史地理,著有《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唐史研究丛稿》、《唐代交通图考》等。
所著《治史三书》至今畅销,是高校历史系入门学习书籍之一。
1996年10月9日于台北忠孝医院因脑溢血逝世,享年80岁。

学术成就
严耕望治学方法严谨,在《治史经验谈》中便自言以“勤、恒、毅、勇、谨、和、缓、定”为学术工作要决,又有“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的格言。
严先生治学方法严谨,他的研究向来建基于庞大的原始文献和细密的考证,如在1956年发表的《唐仆尚书丞郎表》,他反覆考证唐代2680余任尚书省仆尚丞郎,共1116人的详细资料,当中发现唐代重要史籍1200多项错处,成为日后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工具书。据他的学生的忆述,严耕望为不同研究课题以人手抄写的资料卡片累积以十万计。
严耕望穷毕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认为这方面“尤重国计民生之大端”。他计划在有生之年依次撰写《唐代交通图考》、《唐代人文地理》和《国史人文地理》三部巨著。《唐代交通图考》的撰写工作自1946年开始,以考释唐代交通路线和制度为目标,计划累积的资料超过十万件,全书原定十卷,依次出版了《京都关内区》、《河陇碛西区》、《秦岭仇池区》、《山剑滇黔区》、《河东河北区》五卷,凡1792页,超过二百万字,被公认是一部学术巨著。直至他逝世,整个计划仍未完成。
严先生的著作虽然精于考证,但绝不仅仅是传统考证史学的延续,他在撰写地方行政制度史时便参考了研究西方地方政府的专著,关注现代社会科学的新趋向。他对于宏观历史的观念,与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有不少暗合之处,他研究唐代人文地理提出的"全史"理念,与布罗代尔对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余英时先生就曾指出,严先生的著作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史学向现代的转化。
严耕望生性谦逊,在《唐代交通图考》的序文中便自言:“当代前辈学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有一u2018我u2019字存乎笔端。余撰此书,只为读史治史者提供一砖一瓦之用,u2018今之学者为人u2019,不别寓任何心声意识。"
严耕望在学术界有普遍的高度评价。如余英时在悼念文章中就称他为"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
大师风范
淡泊名利
严耕望终身以“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为座右铭,并认为“后六个字极不易做到”,而做不到即不能成为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也不要想在学术上有较大的成就。
1964年,严先生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担任新亚研究所导师。据他的学生回忆,中大当时给高级讲师的举家旅费是坐飞机的标准,而严先生一家则改乘轮船抵港,节省下来的钱以贴补家用。事实上,来港前严耕望的生活已经相当窘迫。当时,在香港高校任教薪金要高出台湾好几倍,然而严耕望赴港更多是出于对老师钱穆的支持,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淘金”。在港期间,为了专心于《唐代交通图考》和《国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和著述,严耕望一如既往地坚持史语所时期的“三不原则”——不兼课、不参加任何活动(包括学术会议、演讲)、不写普及性文章赚稿费,理由是花费时间太多,所得不偿所失。
1973年,香港中文大学有讲座教授一席空缺(香港的大学采用英国制度,每一系只一位“讲座教授”,且为终身制,其余全部为讲师),当时已经是“中研院”院士的严耕望众望所归,然而由于讲座教授需兼行政,而行政工作在他看来对学术研究颇具“杀伤力”,故而这一在寻常人看来能名利双收的位置最终还是被严耕望婉言谢绝了。直到65岁退休,严耕望在香港中文大学还只是一个高级讲师。余英时在《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一文中说,严先生在名利面前这种“澹泊自甘、寂寞自守”的性格和治学的勇猛精进、锲而不舍,恰好互为表里、刚柔相济。这或许就是钱穆先生认为聪明人最缺的“毅力与傻气”吧。
舍命报恩
余英时曾说,任何人曾对严耕望有过一点帮助,他都永志不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钱穆和傅斯年两位先生的感戴,非但是永志不忘,甚至可以说是不惜以个人健康乃至生命回报!
据严耕望的弟子廖伯源回忆,严先生逝世后,夫人段畹兰谓先生平日常自以其生活规律有节制,当可活到九十以上。盖欲长寿以完成其规模庞大之研究计划,诚可谓一科学的工作者。严耕望自年轻时起,就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从不开夜车赶工。然而,去世前一年偏有一次致命的破例。1995年初,台北《史语所集刊》傅斯年百年纪念专号征稿,严耕望认为其一生事业学问,受惠于傅斯年的识拔,所以不顾血压高、中耳不平衡等疾病在身,“拼了老命也要赶出论文以纪念傅先生”。连续两个多月赶写文章,常过深夜十二点才就寝,完稿前几天,甚至工作到凌晨两点多。以近八十高龄一改数十年之习惯,故而文章写完后大病一场,健康状况大大受损,此后常走路不稳,站起会头晕。两个月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为纪念钱穆百龄诞辰,举办学术研讨会。为表达对老师的尊敬,严耕望仍强自振作,每天一早坐巴士去学校出席会议,但在准备讲稿时已明显力不从心,只得对学生说,等过了钱先生的研讨会后要好好休息,待养好精神再继续做研究。当年暑假,医生诊断出严耕望有轻微的帕金森症状,脑部有微血管阻塞。多次医疗与检查,都没有明显的效果,病情时好时坏。1996年6月赴台治疗,期间曾一度病情转好出院,然卒以突发脑溢血送救不治,于10月9日逝世,享年81岁。
严氏晚年最得意的弟子李启文在整理老师手稿时发现,严先生有很多尚未发表的文章其实早已写就(属于《交通图考》第六卷范畴),但他为傅斯年纪念论文集投寄文章时,竟没有使用这些成品,而是就另一课题(唐代人口)重新撰写,显然是想在学术研究上再提供一己之心得,以此诚意报答傅先生当年的知遇之恩。李启文不禁感叹:“可惜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是无可补偿的损失。我曾这么想,归田师由傅孟真先生提拔,五十年后又还于傅先生,似乎冥冥中别有契机。”
史学述略
生平概略
严先生,安徽安庆罗岭镇人,名德厚, 字耕望,号归田,以字行,所谓归田者,取陶野人“归园田居”之意,可见其心意指归大抵在于恬淡自然、不与世事,观其一生治学亦以躬自砥砺、勤耕不辍垂范后世,余英时谓其为史学界的“朴实楷模”,诚然也。先生论著精当,且卷帙煌煌,如《两汉刺史太守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仆尚丞郎表》、《唐代交通图考》等,为现代学人之佼佼者,先生史学思想、研究路数从中可大抵揣度,而先生又著有《治学三书》,尤以示人治学门径为己任,综合数端,先生之史学可概而略述也。
初显天赋
据先生自述其幼年对数理之学颇有天赋 ,又对地理学饶有兴趣,后因机缘而转入史学之门,于民国二十六年进入武汉大学历史系。章实斋有言“学问不可无宗主,但不可有门户”,详绎先生所撰《钱宾四先生与我》,可知先生之学实源于宾四先生。虽然耕望先生很早便专心于制度研究,大学毕业论文的选题即是《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后作为《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的上编上卷出版,但真正为其日后治学方向做了决定性指导的,当是钱宾四先生来到武大后做的第一次讲演: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便是行政制度 。纵览耕望先生所成诸作:五卷本《唐代交通图考》(第六卷为易簧后及门弟子李启文所整理)当属历史地理;《两汉太守刺史表》、《唐仆尚丞郎表》、两卷四册《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当属后者;其他单篇佳作几乎无一例外,晚年所编之论文集,即以上下分篇:上篇述地理,下篇述制度;与此同时耕望先生未能完成的几项研究计划《唐代人文地理》、《国史人文地理》也是围绕着历史地理的方向继续深入的 。对此,耕望先生自己和师友门生也有共识 。
大学时代
严耕望当年在武汉大学读书,他们那一班历史系人数不多,但对于老师的教课非常挑剔,尤其是严先生和他的好友钱树棠,性情生硬固执。所以教授对于他们这一班多感到头疼。系主任方壮猷先生的“宋辽金元史”,前后各班都开课,但自动未给他们讲授。有一次在“史学方法“的课堂上愤愤地说:”诸公十年以后都将是大学教授,就知道也不容易!”新聘的教授更要被挑剔。徐光教授给他们开“秦汉史”与“三国史”,听说他历教北京大学、中央大学,颇有名气,同学们都很高兴。但一开课,他倚老卖老,好像只有他读过很多书。可是他所讲的,不过就《通鉴纪事本末》摘要演述而已,而且很多错误。听了两堂严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指出十几条错误,连同钱树棠所写一篇呈文,经全班同学签名送呈校长,这位老先生就此离开了。到了高年级,他们觉得学校高阶层人事不够理想,将来毕业证书由他们签字,不光荣,希望请朱光潜先生出任教务长。遂请示校长,但校长说:“这是学校行政,你们管什么?你们要请某人担任某职,人家就听你们安排吗?”可是后来朱光潜果然担任了教务长,可能是校长本有此意,两个傻学生的要求不过加强其决心而已!(摘自严耕望:《治史三书》,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7页。)
眼光独到
宾四先生不仅为其点明了治学之路所在,还将一种“通识”的眼光传授于他:“现在人太注重专门学问,要做专家。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一个人无论是读书或做事,一开始规模就要宏大高远,否则绝无大的成就”、“中国学术界实在太差劲,学者无大野心,也无大成就,总是几年便换一批,学问老是过时!”此种“磅薄”的气象、“通识”的要求,正是所谓国学的精髓所在,近现代学人莫不以此为治学标的 ,而此种“通识”又是建立在专家之学基础上的,宾四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到:要先专精某一断代,然后来看通史,在这一基础上重新认识此段历史,续而再挑某一断代大下力气,回来再看通史,这样一段一段延展开来,最终豁然贯通、浑然一体。蒙文通亦有类似的看法 。耕望先生便如此的大力气去实践了,他也是从秦汉入手——这一点颇有宾四先生之风,先生亦曾著有《秦汉史》一书,然而耕望先生似乎对先秦之学未能深下功夫,于宾四先生学历史必以《左传》为柱石的观点 稍有不同——写出了《两汉太守刺史表》等作品,续而又将目光投向又一盛世唐朝,撰写了名著《唐仆尚丞郎表》,其后他又著有《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填补了汉唐之间的制度研究空白,虽然他没有写出通史类的著作但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和《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的合编)和上述其他著作中已经体现了一定的通史眼光,从而在宋以前的区域内完成了从断代到通史再到断代的研究思路 ,这些都是大角度、全范围的研究课题,而鸿篇巨制《唐代交通图考》更是总结性地发挥了这一“专”与“通”、“精”与“博”的治学特色,写出了古代人文地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在《自序》中说:“盖余为学,既详征史料作深入研究,又期广被于面,严密组织,成其系统,特以强毅沉潜,遵行计划,深思虑、穷追索,不畏难辛,不求近功而已,”可谓“夫子自道”。其《治史经验谈》第一篇第一节便是谈“要u2018专精u2019,也要相当u2018博通u2019”,可见耕望先生对此是如何的“情有独钟”啊。
治学精神
如果前两者只是治学方向和治学方法的话,宾四先生更将一种治学精神贯穿其身:“我们读书人,立志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的学者”,这是极高的学术境界。耕望先生于此似乎略有所悟而实得不夥。在撰述《唐仆尚丞郎表》的过程中,耕望先生发现了两《唐书》的若干问题,曾经有意仿王先谦之于两《汉书》对二书作重新校注,同时又因搜录了若干“唐史人文地理”的材料而想就此深入,两难之下,求教于宾四先生,钱先生意在后者:“把一生精力专注于史籍的补罅考订,工作实太枯燥,心灵也将僵滞,失去活泼生机,不如讲人文地理,可从多方面看问题,发挥自己的心得” ,于是便有了《唐代交通图考》的创写。但是,细揣宾四先生的意思,大抵在于有了一定的根基后,大可抛开细密考证的路数,从简单的史学研究上升到对国学全部问题做融会贯通的理解,将自己的精神注入其中,做到“有我之境”,即最高意义上的“春秋笔法”。而耕望先生却仍然用过去的方法,一条路线一个驿站的缀连史料、考订过去,耕望先生也意识到了自己未能达到更高的境界:“余撰为此书,只为读史治史者提供一砖一瓦之用,u2018今之学为人u2019,不别寓任何心声意识” ,故而他也似乎无法欣赏那些具有“有我之境”的上成之作,比如对宾四先生晚年力作《朱子新学案》,他便因不熟悉思想史而不置可否,而对陈寅恪巨著《柳如是别传》更是不屑:“表彰柳如是一人之外,除了发泄一己激愤外,实无多大意义”,“几乎失去理智地作此无益之事” 。在耕望先生看来似乎只有那些可以最后板上钉钉、且具宏大规模的考证类著作才有价值 ,实在是大有偏见,“人”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朱子新学案》、《柳如是别传》都是立意于“人”之精神与“史”之精神的探求,剔除了“人”,所谓“客观”的学问似乎不能算是第一流,故而在其师宾四先生的眼里,他始终只是一个专家,余英时反驳“他已经不是一个专家”的话,大概只能看成他是几个方面的专家。似乎是因对“人”学领悟的不深 ,耕望先生对中文出身之人颇有微辞,他在《治史答问》第十一篇中谈到:中文出身者不可能在史学上有大作为,只能搞学术史研究和史籍校订。如此的说法似乎太狭隘,这和其幼年数理特异而国学功底稍弱大概不无关系。宾四先生在年轻时便熟读《文选》等书 ,其在中学所任之课程都是国文而非历史 ,大凡一流学者莫不是文史淹通,陈贻焮先生著《杜甫评传》不但综合诸家诗作详加编系、参合联串,且于地理、制度无不考订精审,绝不亚于出身史学之人,而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入了杜甫的内心世界,从杜甫的眼中回看唐史兴衰,这似乎就比耕望先生那种简单地运用唐诗材料进行纯粹的史实考订要高明不少。他在学术中始终没有在更高层次上灵动起来,而且也没有丝毫“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的想法,只是一个矻矻终日藏于“中研院”和港大的学者。虽然业已“格物”而“致知”,在学术的高度上难有比肩者,但是似乎少了一份读书人对社会的责任,“治国”、“平天下”的认识在耕望先生身上难以寻觅。
独特风格
如此看来,耕望先生似乎只是部分的继承了宾四先生的学问 ,但却有着自己的风格。从他的诸多著作以及《治史三书》中,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其所勤勉一生的学术诉求就是“朴实”,而其所获成就便在于最大可能地复原了某些史实。他在《钱宾四先生与我》中多次谈到自己非常愚笨,不够灵活和机敏,而宾四先生则鼓励他:“大抵在学术上成就大的人都不是第一等天资,因为聪明人总无毅力与傻气”,他于此受益菲浅“除了学术方面的引导与诱发,教我眼光要高远规模要宏大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于我的鼓励”,在这种激励下,他根据自身情况摸索出了一套十分朴素的研究方法:
其一:坚持用史料说话,“正史、政书及地理书之外,子、集、金石、简牍、类书、杂著等,诸凡当世或稍后有关之材料无不旁搜掇拾,取供考订”,不仅如此其对佛藏、笔记、稗官野史也颇为留意。而又尤重正史,所谓“治中国史,正史仍为最重要之史料” ,精读耕望先生诸作,可见其对历朝正史特别关注,如《两汉太守刺史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唐仆尚丞郎表》,几乎大都使用正史材料,在世风纷纷唯新材料是求、慨叹可见史料发掘殆尽、不屑于精读正史的当代 ,这一做法无疑具有极佳的拨乱作用。在研究过程中耕望先生不但近乎完美地做到了地毯式搜罗材料,他对选题的研究情况也是了如指掌,耕望先生《唐仆尚丞郎表·序》中短短几行字就把唐代中央行政制度研究情况的大概清楚地做了交待,“未入其门,先闻其声”,这使得研究者在一开始就对该书的研究价值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虽然现在的学术著作和论文都有“学史回顾”的要求,而与之相较,眼光大抵狭隘许多,而在具体的考证过程中,又厘订和纠查出两《唐书》和既往研究中的几千条错误,这样已经不是被动的接受和采用材料,而是辨正地考索史料,在更高层面理解史料,从而在坚实和灵活两个方面全面挖掘出可见史料的价值。
其二:在细读文献过程中,“聚集许多不相干的琐碎材料、琐小事例,加以整理、组织,使其系统化,讲出一个大问题、大结论”。纵观耕望先生诸著,正可见出这一研究轨迹,如在《唐仆尚丞郎表》中,耕望先生仿照杜佑《通典·职官》的书法,按照官职等级,从“仆射”到“仆丞”、从六部“尚书”到“尚书侍郎”,将各种史传记载中的人物逐层系于官职之下,又将细密排比后的材料,缀于各人之下,如庖丁解牛一般将有唐一代中央“八座”行政制度的具体情况悉数解开;他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如法炮制,先标出一职位如“刺史”,后系若干史料以期说明“刺史”之诸多问题,然后再续说其州府佐僚,并系若干史料来说明“州府佐僚”之问题,这样如掰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深入进去,并与相关的“都督”问题比较阐发,从而对整个制度做了揭底性的细密研究;在《唐代交通图考》中他先描述一条交通线,然后结合驿站,一段驿程一段驿程的详加征引考订,再将所考驿程串连成线,极其清晰地揭示出若干鲜为人知的史实,续而再将若干条路线编织起来,形成了一张大网,将一幅生动的唐史画卷展现开来。耕望先生能够如此绵密细致、条分缕析地梳理和排比史料,似乎与其少时尤精数理不无关系,他在具体研究中经常不自觉地使用一些排列组合的方法,如在侨州郡县与实土诸州郡县的关系问题时就不厌其烦地列出了几种可能情况,其在考订长安洛阳交通线问题时也如是将华、虢、陕州之间的道理排比组合 。用如此缜密的思维进行精细全面地考订,自然收获丰硕、成果卓著,而且根基牢固,几乎无懈可击,如《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 一文彻底理清了《通典·职官》中模糊误谬之处,揭示了唐代尚书省与寺监百司之间的关系变化,尚书省内部仆、尚、丞、郎之间的权利演变消长,从而可以更加清晰地鸟瞰整个唐朝中央行政制度的运动发展;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发前人未发之覆,揭示出魏晋地方行政制度中,除众所周知的州、郡、县三级,另有更高层级的都督区为人所忽视;《唐代交通图考》更是在精熟材料的基础上,复原出了唐代交通路线的重要部分;这样如此辉煌的成果,实堪“大问题、大结论”之称,怎不令人叹为观之。
其三,持之以恒,至死方休。耕望先生于一九九六年十月因脑溢血而病逝,他在归返道山前三个月写给友人钱树棠的信中称:“我由去年正二月赶写一篇论文,耗费精神太多。自后头晕屡发,精神困顿不堪。又患上u2018百经逊u2019病,精神更是困顿不堪。近来策仗而行,亦是寸步难移,几乎随时可倒下……” ,而常日又是“每天工作,从不间断,故无所谓星期六、日休息” ,可见耕望先生确是耕耘到死学方止。回看耕望先生所成诸作,几乎都是引证浩繁、体大思精,若没有长期不懈的努力做基础,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做支撑,怎会有如此的成就?余英时在《中国史学界中的楷模》一文中说:“(《唐代交通图考》)在西方和日本都只能出之于集体实践之一途,即由计划的主要执行人指导一、二十个助手分头进行。现在耕望则以一手之力完成之,他的恒心和毅力真足以惊天地而动鬼神了。”在学术界至为浮躁和腐败的今天 ,耕望先生这种学术追求的纯粹精神、真理探究的忘我境界无疑对整个学界都是振聋发聩的。
上述几点,只是就大处着眼来看,其他具体的方法门径,《治史三书》言之详矣,可哺枵腹。耕望先生虽操劳终身,却每每不忘提携后学、解疑示迳,既显学问渊源有自,又望精艺后继有人,张载所谓“为往圣续绝学”者,先生是也。
主要著作
一、专书
两汉太守刺史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30 , 1947 。
唐仆尚丞郎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36 , 1956 。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45 , 1961 。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乙部:晋魏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45 , 1963 。
原刻景印石刻史料丛书 甲乙编,严耕望辑,台北:艺文印书馆, 1966 。
唐史研究丛考,香港:新亚研究所, 1969 。
治史经验谈,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1 。
治史答问,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5 。
唐代交通图考卷一至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83 , 1985 。
严耕望史学论文集选,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1991 。
钱宾四先生与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2 。
唐代交图考卷六,严耕望遗著,李启文整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3 , 2003。
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严耕望遗著,李启文整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05 , 2005 。
唐代交通图考—第一至六卷引用书目及纲文古地名引得,严耕望遗著,李启文整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83 , 2006 。
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6 。
二、论文
两汉郡县属吏考,《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 2 ( 1942 ): 43-94 。
楚置汉中郡地望考,《责善》 2.16 ( 1942 ): 8-12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武帝创制年号辨,《责善》 2.17 ( 1942 ): 7-8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楚秦黔中郡地望考,《责善》 2.19 ( 1942 ): 9-16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论秦客卿执政之背景,《责善》 2.20 ( 1942 ): 4-8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秦宰相表,《责善》 2.23 ( 1942 ): 4-11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两汉郡县属吏考补正,《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汇刊》 3 ( 1943 ): 13-18 。
北魏尚书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8 ( 1948 ): 251-360 。
北朝地方政府属佐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 ( 1948 ): 267-324 。
魏晋南朝地方政府属佐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0 上( 1948 ): 445-538 。
汉代地方官吏之籍贯限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2 ( 1950 ): 233-242 。
秦汉郎吏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3 上( 1951 ): 89-143 。
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与地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4 ( 1953 ): 1-68 。
略论唐六典之性质与施行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4 ( 1953 ): 69-76 。
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5 ( 1954 ): 135-236 。
汉书地志县名首书者即郡国治所辨,《中央研究院院刊》 1 ( 1954 ): 19-39 。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略,《大陆杂志》 9.8 ( 1954 ): 237-243 。
唐代人文地理,《中国历史地理》册二,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出版委员会, 1954 。
杜黄裳拜相前之官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6(1955):309-313。
魏晋南朝都督与都督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7 ( 1956 ): 47-105 。
旧唐书夺文拾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8 上( 1956 ): 335-362 。
旧唐书本纪拾误,《新亚学报》 2.1 , 1956 。
唐代纺织工业之地理分布,《大陆杂志》 13.11 ( 1956 ): 341-344 。
唐宋时代中韩佛教文化之交流,《中国佛教史论集》册一,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 1956 。
从南北朝地方政治之积弊论隋之致富,《新亚学报》 4.1 , 1959 。
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0 下( 1959 ): 689-728 。
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庆祝董作宾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四种, 1961 ,页 643-679 。
北魏军镇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4 上( 1962 ): 199-261 。
两汉郡县属吏考补正,《金陵齐鲁华西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 3 ( 1963 ): 13-18 。
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5 ( 1964 ): 301-319 。
景云十三道与开元十六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6 上( 1965 ): 115-121。
唐代方镇使府军将考,《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上册,台北:清华学报社, 1965 ,页 259-274 。
唐代方镇使府之文职僚佐,《新亚学报》 7.2 , 1966 。
汉唐?斜道考,《新亚学报》 8.1 , 1967 。
唐上津道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8 ( 1968 ): 285-292 。
唐骆谷道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9 上( 1969 ): 15-26 。
唐蓝田武关道驿程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9 下( 1969 ): 1-26 。
唐金牛成都道驿程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40 上( 1968 ): 215-254 。
通典所纪汉中通秦川驿道考,《新亚学报》 8.2 , 1968 。
唐代茂州西通吐蕃两道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1 , 1968 。
唐代洛阳太原道驿程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2.1 ( 1970 ):5-34。
唐代凉州西通安西道驿程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43.3 ( 1971 ): 335-402 。
唐代长安西通凉州两道驿程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4.1 ,1971 。
唐代长安东北通胜州振武军驿道考,《新亚学报》 10.1 , 1973 。
唐代关内河东东西交通线,《新亚学报》 10.1 , 1973 。
唐代安北单于两都护府考,《钱穆先生八十岁纪念论文集》,香港:新亚研究所, 1974 。
唐代河湟青海地区交通军镇图考,《新亚学报》 11 上, 1974 。
唐代滇越通道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8.1 , 1976 。
汉晋时代滇越通道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8.1 , 1976 。
唐代北庭都护府通西州伊州诸道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8.1 , 1976 。
唐代黔中牂牁诸道考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50.2 ( 1979 ):361-380 。
北朝隋唐滏口壶关道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51.1 ( 1980 ): 53-69 。
隋唐永济渠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53.1 ( 1982 ): 21-56 。
唐代盛时与西南邻国之疆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59.4 ( 1988 ): 957-976 。
中古时代桐柏山脉诸关道,《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与考古组》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 1989 ,页 651-674 。
《元和志》户籍与实际户数之比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67.1 ( 1996 ): 1-4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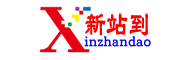 新站到阅网_Xinzhandao.COM
新站到阅网_Xinzhandao.COM

 张铭心 个人简历介绍
张铭心 个人简历介绍 曹三公子 个人简历介绍
曹三公子 个人简历介绍 梁其姿 个人简历介绍
梁其姿 个人简历介绍 严耕望 个人简历介绍
严耕望 个人简历介绍 冉万里 个人简历介绍
冉万里 个人简历介绍 姚崇新 个人简历介绍
姚崇新 个人简历介绍 孔祥吉 个人简历介绍
孔祥吉 个人简历介绍 黄纯艳 个人简历介绍
黄纯艳 个人简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