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简介
祁梦君,男,原名祁陆军,1973年生,山西晋城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员。1990年3月入伍,1991年开始文学创作和新闻写作,主要作品有大型报告文学《长路当歌》、《喝退太行山》、《大爱无疆——5.12汶川大地震记实》等,作品散见于《中国诗人》、《民族文学》、《中华新闻报》、《中国食品》、《黄河》、《作家文摘》、《发展导报》、河北电视台、河南经济广播电台等,入编《中国诗人大辞典》、《新世纪实力诗人文丛》、《中国青年艺术家传集》等选本。
诗人影响
中国的诗歌有着其特定的多重身份,在整个文学流派繁荣或者堕落的今天,我们很难从真正意义上读懂其必然的结果。诗歌是需要责任的,就如同诗人的责任一样。诗歌至五四运动以来路越走越窄,虽然期间也有过有关诗歌的大讨论,尽管这些讨论曾经产生过局部的好的影响,但总的来说,诗歌越来越沦落,越来越成为一些人把玩的风标。诗歌没有了它应有的激越与慷慨,没有了它特有的温情与细腻,所有的作品呈现出来的均是一种失态的病体。在这种诗歌语境里,一切都变的模糊,一切都变的不可依靠。
九十年代末,一批以怀疑的目光向着扭曲的现实发出抗议与质问的作品出现在中国诗坛,他们充满锐气的创作实践对当前大陆文学起到了巨大的震撼作用,他们的作品因承载了社会的忧患而获得了公众的同情与承认,这种对于苦难和悲情的表现,不仅调整与完美了诗歌本身,也使得读者因为诗歌传达了他们的憎爱而亲近并肯定了作品本身。这其中,山西诗人祁梦君的诗歌以其久违的人性和闪光的人道思想,以及对中国时下长久空缺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紧密联接了社会的脉搏和公众的情感,以它的真实性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其作品因传导了人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念而成为了现实生活的血肉组成部分,引起广泛的关注。
对于这个来自山西本土的诗人来说,他的作品代表着他自己的一切。祁梦君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相当自觉的诗人和诗歌承担者,在他的诗歌里,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生存、搏斗、欲望、破灭,他善良、正直、勤奋的性格,让他的诗歌随处显现着一种不屈的力量,读他的作品,更多给予我们的是坚强,他对社会、对人性直接的透视让人感到恐惧与担忧,当他用文字表达出来的时候,我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成熟的诗人,同时也看到了一个勇敢的斗士站在荒凉的草原对天长啸。“我一直行走在诗歌绝望的边缘,我不知道我写的什么,但我知道我在干什么”这是祁梦君写在他自己博客上的一段话,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年轻的诗人内心的焦虑与无奈。
台湾著名学者陈思娴在《用感恩的心透析梦君其人其诗》一文中说:祁梦君的诗歌以其久违的人性和闪光的人道思想,以及对中国时下长久空缺的批判意识和怀疑精神,紧密联接了社会的脉搏和公众的情感,以它的真实性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其作品因传导了人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念而成为了现实生活的血肉组成部分,引起广泛的关注。是的,祁梦君是一个感性很强的诗人,虽然他的生活一直处与行走与漂泊之中,但他灵性的思想之光却始终站在了人类精神的前沿,我们可以不去读他的作品,但我们不能无奈地跟随着他思想的流浪而海角前行。

由于生活的变更祁梦君的诗歌写作也发生了改变,正如著名旅美诗人马嘏所说的,“这些年来,祁梦君似乎是为生存奔波过多,给写作留的时间和精力少了。他的写作一直在变化着,早期的放荡、空灵,现在则沉重、大气。也正是由于他长期的漂泊使得他的作品在当代诗坛显得近于完美和奇特。太多的诗歌作品轻浮而无味,当许多人把诗歌写成一种玩弄文字的游戏并成为一种时尚的时候,祁梦君的写作中依然携带着丰富的情感、与生俱来的悲剧意识走在我们空无的生活。他的作品透露着某种清晰和坚硬并且与生存现场发生紧密的摩擦:
一些风,穿过山口
我解开下落的谜
走着,在冰凉的大地上
一些孕育许久的伤
渐渐长大,如一片林
我看不清,下落的雨
在冰凉的大地上奔跑
渴望一些,风干的柴
烘烤潮湿的心
在冰凉的大地上奔跑
身后,不见来者
只有身前追赶的路
——(《我在冰凉的大地上奔跑》)
精神的无奈、未来的渴望,祁梦君的诗歌世界无疑是复杂的,它所呈现给我的印象更像是太阳下一个倔强和沉重的背影,那透过光阴和重压所失落在我心田的该是着怎样的内心的世界?在诗人身上呈现出太多的孤独、隔绝和无望的悲情,正如我的朋友、德国著名作家蒙西·罗西今年来北大时所说的,文学是精神折磨的一种语言艺术,而作家更多地是应该来承受和担当这种心灵上的沉默。由于社会日益加剧的分裂,快速的现代生活节奏,当无边的贪婪与名利追逐的欲望之海不断冲击我们小小心湖的时候,诗人个体的隔绝化,就使得他的作品与这个时代猛烈碰撞的可能性愈来愈不可回避。
写于2007年6月的长诗《我在黄昏里看见了我的墓碑》无疑成为祁梦君在面对无边的困惑与生活的磨难时发出的对生命的怀疑,是他内心隐忧和焦虑灵魂的呐喊。这首诗歌用悲痛的语调将一个处与极度困惑与忧伤中的诗人以渴求的生存和精神的亮光在晦暗的背景上倔强地闪烁。当他生存的复杂的而维度向上的精神艰难的向前延伸的时候,吁求、渴望、坚忍、自问、盘诘就充满了空前的张力与冲突。
我是否还能携你再一次,走进那山的背面
我能否拒绝一根火柴引燃的
意象。在你为我守候的酒神面前
你可以想象我的陶醉
我在黄昏里看见了我的
墓碑。雪,落满京都,我在
一片枫林里寻找思念。大片的云朵,飘过
谁愿沉睡在我的掌心
——《我在黄昏里看见了我的墓碑》
在祁梦君的诗歌作品中,他创作于2008年春节期间的《雪殇》所为读者创造的沉重语境是常人所不能体会的。他在寻求着能够读懂他的人,也希望他能读懂别人,当希望在他狂热的追求中一次次远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只能是属于祁梦君自己的个人化的白色的世界,这种个人化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他诗歌理想时代终结的最后霞光。这种令人抬头仰望甚或垂泪的光又使一个灵魂在灰暗的背景中振颤不已,这些痛苦、尴尬的诗句将一个年轻诗人的内心伤痕抹去,疼痛的岁月用无法言传的语言将70后一代人的尴尬或者命运至于一个荒芜的原野,风干并且撕的粉碎。穿越爱是苦难的,对于祁梦君而言,对于一个正在历经沧桑磨难的人来说,诗歌写作永远是狭窄的,这是否是祁梦君今生注定的命运?我不知道,也不敢去想,一个年轻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他的悲痛、他的忧伤、他的沉重的、真正的内心世界竟然让人不敢去猜测,难道那脆弱的不仅仅是他的情感?
一切都沉默在无边的夜里
可以忽视一场雪崩的到来,还可以
把这些孤僻的声音揉进梦里
让无谓的街灯照亮逐渐倾斜而下的楼梯
一个人醉酒后回家,还可以关闭车灯
等一些光拉长的距离无限延长
我习惯于在黑暗中左手握着右手的感觉
习惯于在午夜时分听楼口骤然响起的笑声
我常常想象着今晨的这场雪
会不会埋葬回家的路
目光远离了阳台,飞身而下
由衷赞叹这场百年不遇的雪
依旧纷纷扬扬
——《雪殇》
这该是一种怎么折磨人的悲伤,这该是一种怎样的磨难?诗人梦君是乐观的,他的乐观伪装了他内心无边的痛苦,我们不知道他的痛来自何处,我们只知道,当生活的不幸与他如影随形的时候,他微笑的脸上始终绽放着阳光般的笑容。
不待回眸的瞬间,雪纷扬而下
归乡的人坐在雪前暇想
一串晶莹的珠下落,点点滴滴
湿透往昔的窗幔
那时候,山叠纵而来,又连绵而去
如今夜的大雪望断太行
钻入心尖的不是风,不是曾经行走的海滩
次第而过的是母亲深夜中传来的叹息
妈妈。没有江风渔火让我对愁而眠
没有两岸猿啼让我轻舟万里
我独守的地方是你望不到的黄尘
只有山风不断,只有一灯如豆
妈妈,此刻我只想躺进你的怀里
听雪落地而动的声音
把笑容挂上你消瘦的额头
在你轻唱的歌里安然入睡
——《雪殇》
在祁梦君的早期诗作中,有为数不多的对白形式语言行走在他的诗歌中,这对于年轻的祁梦君而言,这种灵魂的对话和撞击也许是他生命最痛苦的时候一种释放。他在2000年创作的长诗《上帝堕落了,我去寻找地狱之门》中,祁梦君和高贵的不幸的上帝的对话和其间沉重的黑暗一起,无疑成了祁梦君那个时期的代表之作。
我终于还是死了
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女孩
用她年轻的母亲沾满精液的内裤
套在了诗人同样年青的脖颈上
她告诉我:
上帝说了,让你死!
我说我没有错啊
上帝为什么让我死
小女孩生气了
她狠狠地将一只硕大的乳罩
砸在了我的脸上:
问它去吧 笨蛋
你真应该是个瞎子
我惊呆了 默默地
跟着小女孩走进了那个
白色的房子里
站到了上帝和那个白灵灵的女人面前
我向上帝述说了我的不幸
并告诉他们说我是个诗人
希望上帝能够为我做主
作爱的女人用她纤细的手
搂着上帝的腰
对着仍在蠕动的他高叫着:
挖掉他的眼睛 让他滚
你真应该让他下地狱 上帝
——《上帝堕落了,我去寻找地狱之门》
在一个无耻、卑鄙、下流、堕落的上帝面前。年轻的诗人竟然无言以对。我们现在无法想象当时的祁梦君是用怎样的心情来写这个作品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足以用灵魂虔诚地仰望的上帝,竟然也被无耻地堕落成这般摸样,这个世界还有什么能够让我们用心去珍藏,还有什么地方是我们心灵安放的天堂?在《《上帝堕落了,我去寻找地狱之门》中,诗人超乎常人的想象将一个个堕落、麻木的灵魂和个我命运紧密相连,并努力使这首诗更具有张力和个人性的自叙色彩:
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对于我们也许原本就无须上帝
寻找天堂 谁下地狱
没有上帝
天堂与地狱还有什么区别
站在上帝面前
我同我的灵魂含泪分手
灵魂啊 你是应该留下
把上帝带走
告诉人们不要为我伤心
天堂失落 我去寻找地狱之门
上帝堕落了还有我们自己
诗人死了
但他的骨头还站着
这
也就够了
——《上帝堕落了,我去寻找地狱之门》
著名诗人北岛曾经用《太阳城札记》这样的诗歌文本表达了属于北岛一代人的墓志铭,而祁梦君的《天堂》在不期然中呈现了他诗歌写作和生命体验的双重忧虑:
如果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
都开满了鲜艳的玫瑰,谁还会
在寂静的夜里,总写着忧伤的
诗行。每一滴泪珠都是一片
飘落的花瓣
奔腾的马群图腾了草原
谁还会守候爱情,还会
在孤独的时候
反复吟唱那首古老的歌谣
看着长夜一点点消瘦在黎明
让等候的筏漂向一座无人的
岛屿
谁都会有幸福的渴望
谁不曾有梦的翅膀
谁愿意守着一畦蛙声
把心埋葬。谁不想把爱情
写在脸上,笑出灿烂的阳光
在生活的花儿凋谢的时候
挂满思念的轩窗
——《天堂》
是啊,如果我们拥有了鲜花,我们就不会写着那些忧伤的歌守住黑夜的出口,如果我们拥有了爱情,谁还会唱起那支古老的歌谣?诗人用反问的语式,向我们不断呈现了诗人沉潜、自省、冷峻和反讽的一面,在一个无限加速的时代诗人提前领受了这个时代的寒冷和无处不在的阴影,在无处不在的沉溺的脏臭的沼泽前诗人停了下来。
从祁梦君尤其是他近期阶段的写作来看,大量关于死亡的话题引起来不少读者的注意。前些时候我们关注到网络上有关他的消息,对他的打击在我看来是不能承受的,我甚至担心这个一直生活在忧郁和痛苦中年轻的诗人是否还会走下来,是否能够抗过这次劫难,这种毁灭式的攻击足可以让一个再坚强的人走向绝地,可以将一个年轻的诗人葬送在他本已绝望的山谷。作为一个时刻关注他的文学朋友,我不可能对他的事不给予过多的帮助和支持。于是,当他依然处在风口浪尖的时候,我写了这篇短文,希望能给予他勇气与希望,正如他在《悲情太行山》中所言“对诗而言/尊严无需调解/面对庄严/我用我的诗歌作最后的陈述/为着黎明/我要向长夜宣战/就算倍爱冷遇我也绝不出卖自己/如果真的从此死去/我也会快乐而自由地生活在/所有爱我的人们/善良的心间”。祁梦君永远也不可能是成为死去的海子,因为任何一个真正的诗人都不可能被同化,祁梦君更是如此,他的坚强、正直,他为生活付出的,已经成就了祁梦君独特的个性。
没有人可以真正走进他的心灵,没有人可以真正读懂他自己,而他所面对又将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我幻想中的村庄,那是我的王国
用诗歌的语言谁能准确地表达,一些细节之后
远逝的芳华。男人,或者女人,祖辈遗留的灶堂
在寒风中显现原始的荒凉,一个季节的苍老,远比
一座山的生命漫长
有时语无伦次。我清醒在一个又一个
错误的黑夜或者白天。我想象不出
一晃而过的秋。一晃而过的霜
那袭红衣,穿透心房,谁的眼泪飞在山外
就在这样的夜写这些无聊的诗歌
我看不见的春草舞动彩纱,看不见
大雪覆盖的白松。眼睛睁着,嘴巴闭着
世界伸手不见五指,无论是归乡还是远行
我都无言以对
向前。粉身碎骨。
向后。无处葬我。
——《太行谣》
这是我看到祁梦君最后的一首诗,诗歌被一种巨大的绝望和绝望所覆盖,行走在这种万劫不复的境地的诗人,内心的悸动与感怀在无限地蔓延、扩散。他思想的河流在干涸的时光中渐渐回归于荒芜的河床,这些充盈的水滴漫洇,迂回,留下的只有阵痛与回忆。向前是死,向后是死,他的痛苦该是怎样的沉重?我们不愿意看到这样的诗行,不愿将死亡悲剧上演在这个本就伤痕累累的诗人身上。但,谁又能帮他走出这黑暗的荒原,谁又是他内心真正的青莲?面对死亡的召唤人往往是脆弱的,那些从天际划过的彩霞曾经燃烧的火焰,终将会在岁月中化为灰烬。无边的伤痛必将走近我们每个人短暂的岁月流痕,好好活着,是我们每个生命基本的渴望。在这里,梦君的《太行谣》给我们展示出来的除对生命的留恋,更多是他对命运绝地的抗争。
拿出什么样的理由来分解我的罪恶
没有了拿刀的手,谁还能用牙齿咬碎太行
现在已是冬天,不见的霜白,唯有秋寒
赶着满坡的石头走过春夏越过秋冬
把我陈旧的衣衫挂上树梢
还是拨起那片错插的竹林吧
在春塘醒来的瞬间让我呐喊
没有埋葬我用什么来超度今生
没有今生,我还能拿什么来埋葬自己
那些忧伤或者死亡
——《太行谣》
面对纷繁复杂、贪婪无序的世界,我们真正能够拥有的只有平静,平静地生活,平静地看待不幸与死亡,当我们面对浩荡的时间形态时,所有的名利只是微渺的,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自己生命最终的归宿,并为自己的归宿捡拾自身足以祭奠我们灵魂的微粒,并从中来感悟我们困惑的人类自己。
作为一个孤身北漂的诗人,祁梦君在北京的生活经历无疑为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更多的灵感和实践,同时也使得他在面对这个多元化世界的时候,有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分析。对于祁梦君而言,诗歌是他承担内心隐忧抑或欢乐的唯一方式,也是他打开天堂和地狱之门的唯一钥匙。文学是孤独的灵魂安息的家园,诗人是孤独的家园里永远行走的灵魂。梦君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他的诗歌和欣赏他的人们。
无知写作,当前诗歌创作的最大败笔
今天参加这个诗学研讨我没有进行准备,本不打算说什么。但是,刚才听了几位朋友的发言,就想说几句。之所以想说,完全是因为对在座的同学们的负责和对诗歌当前现状的担忧而决定的。法国著名诗人密茨凯维支说:“诗人不仅要写,还要像自己写的那样去生活。”
这是我今天送给同学们的第一句话。
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注意到一种现象,现在的中国,没有比写诗更容易的事了,套用一句刚才那位戴眼镜小女孩的话就是,作家满街走,诗人多如狗。呵呵,如果有人现在站起来反对,我也能够理解,因为中国人最痞的不是地痞流氓,而是诗人作家。公刘先生说过一句粗话,“诗人简直和上公共厕所的人一样多,诗就不过是排泄物,人皆有之。”但是,说一句大不敬的话,我相信人是有猴子变来的,但我决不相信现在的猴子会变成人。所以,就有了我的第二句话,李白死了,老杜也死了,几千年过去了,诗歌还是诗歌,你就是你自己。
最近我接触了一些认为诗歌写的不错的男男女女,暂不说他们诗写的如何,仅他们对诗歌的态度,就让我感到震惊。他们除了保持着个人写作的风格特征外(这中间包括一些当前网络中非常活跃的中青年诗人,如李长空的清逸,李晓泉的舒展,阿务卓林的奇崛,竹露滴清响的明丽,惠儿的柔曼、谷风的厚重),还普遍带有以下几种色调:
一是对敌视和虚化日常生活、远离自己每天置身其中的生存现场、在一种假想中完成自我感动的写作形态保持着强烈的义愤和警觉,他们抱着一种特定的使命感,以用行为写作为荣,他们不理解“梨花体”、“零距离”甚至“负距离”写作的内质,他们笔下的每一个字,几乎都带有一种责任,他们不观旁、不媚态,不故作学问、不无病呻吟,在他们眼里,诗歌是圣洁的象征,不是卖狗皮膏药,可以无知、可以无责,可以自娱。
二是他们拒绝虚伪写作,提倡诗歌与社会的结合,反对生涩、故弄高深,把本来朴素的情感搞的扑朔迷离。他们都有着一颗纯净的心灵却一直被世俗所困扰,他们高喊着艺术无畏却一直在做着保卫艺术的斗争,而真正的诗歌又让他们痛感诗之无力。于是他们的笔端情不自禁地流露愁苦和悲伤,而就是这种悲伤和愁苦却散发了一种特殊的魅力。
三是他们都善于兼容,天然地支持一切后来者的探索与尝试,却往往招来非议,那些在写作上抱有机会主义者的人是根本不会理会他们的立场与观点,甚至有人以无聊的行为来解释某种人为的诗歌现象,这不能不算是我们这个时代诗歌的悲哀和憾事。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多地指望他们这些人做什么。佛说,每个人都只能拨亮属于他的那一盏灯,照亮他脚下那一小片地方。这就是长空们的局限性。他们本身非同寻常的经历造就了他们非同寻常的诗歌,这也许是可以多少慰藉我们这个时代的东西。
诗歌作为人类表情达意的主要形式,它直接反映的是作者内心最深的感受,而这种感受无论是从语言还是组织都形成了它传达的特殊展现方式,而这种方式是通过人的行为来实践的。
公刘认为,诗歌在艺术技巧上不能再耽恋与华丽与精巧,那种玩弄文字游戏的写作其实是一种较底层次的东西,其目的就在于掩盖作者内心的空虚与知识不足。我认识一个叫(略去姓名)的人,说心里话,她的诗歌没有几个人能够看的懂,但却发了不少,甚至《星星》、《绿风》、《诗选刊》等一些国内大刊也发了,而且她还跟我说非上《诗刊》不行。今天在座的都是比较优秀的青年诗人,我相信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听了这话都觉得这人不是个搞写作的人,怎么看都象个铁匠。刚才你们也看了她的一些东西,我也听了大家对她那些作品的讨论,都很中肯。刚才惠子问我,诗歌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我们写作的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在你们日本是怎样来回答这些问题的,说心里话,从刚才你们读的那个女人的作品中,我相信大家也许已经明白了什么。我个人认为,诗歌是启迪人类灵魂的语言,是能够拨动人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那根琴弦的一种倾诉,并且能够让它弹奏出尘世间最美的音符。因此,真正的写作应该是朴素的,最朴素的东西往往是最真实的。公刘先生的话说的最好,那种故意把诗搞的如猜谜一样的人,其实是为了掩饰他内心因无知所造成的文化缺位和想象贫乏的恐慌。就刚才大家所读到那几首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我们总觉得她的学问做的很好,但细细品读之余,你就会发现,那只是一种把文字进行游戏而实质没有任何必要的无关形象而已,其作者本人也未必能对她的作品进行可信的释义,也不可能作出合乎诗学的解释来。我把这种诗歌写作叫做“无知写作”。无知写作最大的特征就是作者本身知识的的严重缺乏,对文学的基本理念仅有基本的接触,甚至根本就不懂什么是诗学。他们鄙视诗学的理论再造,反对诗歌创作的基本风格定义,其本身即不学无术,自恃强态,其创作的动机是为了写而写,并带有强烈的功利性(我说明一下,这种创作和功利性写作有着一定的联系,但它比功利性写作还要低级。起码,功利性写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学素养,而无知写作则是一种滥竽充数式的把戏而已),写作的特点是以生涩难懂的语言作框架,刻意寻找古怪的词语来强行填充诗歌的意象语境,不断追求文字无聊上的变素,根据表现内心的情感需要,随意地选择没有事件性关联的形象,“他们的诗往往细节清晰,整体散乱,诗中的形象只服从整体情绪的需要,不服从具体的、特定的环境和事件,所以跳跃感强、并列感也强,但这是种对诗歌情节性的轻视,也是作者缺乏对诗歌创作明朗化的理性思考,其作品的感染里力与语言渗透力是虚假的,也是缺少文化底蕴的一种最直接的表现。”(——公刘语)故弄玄虚,故作深沉,轻率而浮躁是刚才你们所看到作品的显著特点。如果说连她自己都无法释义的诗歌让读者去评判,这是不公平的,最终也只是文学历史长河中的“死胎”。
当前国内一些诗歌媒介在选稿的立场上已经远远偏离了诗歌的本质,他们似乎看重的是另外一种无形的东西,综观近年来《星星》、《绿风》等专业刊物所发稿件来看,这种人为操作的痕迹屡见不鲜,一些写作者已经把写作当作一种向人卖弄的技巧而招摇,一些诗歌编辑也已经把审编的责任用以换取个人利益的筹码。真正用心在写的人,那些真正代表时代精神,反映大众情绪的作品已经不多见了,随之出现的就是大家刚才看到那些无聊的、献媚式的呻吟。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诗歌现状和文学的绝境。
诗歌的历史是伴随着人类的历史成长起来的,她的发展与人类的语言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诗歌发展到今天,其表现形式与主题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前诗歌界有着一种通病,装腔作势的人大有人在,满纸的悲戚只是鳄鱼的眼泪,其实他在写作的时候是笑着的,这种虚情假意入诗,只能让后人觉得恶心与不耻,他们最善于的是,一会炫耀自己好象特别有文化的那种,把他根本没有搞懂甚至只是看了一个名字的马奈、凡·高罗丹入诗,一会儿又把俄狄浦斯情结、自由落体等拿进诗中,我们当然觉得诗所涉及的知识面越宽当然越好,但是,要用的恰到好处,而不是故意买弄。真正的“一首好诗,究竟是靠从心灵中流淌出来的内在之物取胜,还是靠外部安插上去的附加物取胜?究竟是以感情动人取胜,还是用生涩难懂、凭蒙骗唬人取胜?这涉及到诗人对诗的态度,对生活的态度和对读者的态度。”一般来说,这样的人热衷于搞花里胡哨的东西,他们既不尊重自己,也不尊重别人,漠视他人的存在,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人也捧为诗人,那诗人也太掉价了。不用多久,也不用再等到下一代,这些所谓的诗歌就会被人们忘的一干二净。可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些作品却每天充斥在一些重要诗歌刊物里,最可惜的是,本来很有才华的一个女孩子,竟然也写起了这种东西,作践起了自己,将大好时光抛在了垃圾之上却毫无察觉、毫无愧色,一切规劝都不入耳,君复何言?
同学们,中国诗歌在近一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一直处在一种模仿之中,它在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传统向现代汉语转变时却遇到了语言和文化的双重对抗,中国新诗像一个病入膏肓的女人,需要神医来拯救它,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已没有了它应有的蓬勃生命之力,各种人等混杂其中,怀着各种目的的人对诗歌创作进行了掠夺性的侵占,诗歌艺术已经沦落为一种妓女艺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壮?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的生活里不能没有诗歌,诗歌也离不开那些喜欢他的人们。我们写诗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有品位的人,应该真实地生活,像小草一样地活着。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到生活的魅力,感受到艺术的无穷魅力。诗坛破落不等于诗歌破落,也许我们无法也无须拯救诗坛,但,我们应当拯救我们自己,拯救诗歌已入膏肓的躯体,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应当坚持并传承的永远的义务。
后赵树理写作:一个垃圾堆上的理论:1s
©凤城论坛 -- 我的凤城论坛,我的天地 -CO
Cz
©凤城论坛 -- 我的凤城论坛,我的天地 =+P#N
《山西日报》近期刊发了一篇题为《后赵树理写作现象瞩目:山西文学评论家对话录》的文章,正如其题目所言,该文本作为山西评论家就当前山西文学创作现状进行的总结性发言,其内容无非还是重复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老话、套话,假、大、空话,无非是在为僵死的山西文学跳一跳、摇一摇、喊一喊,其文本内容让人感到可笑而可悲。LxsH|4
文章开篇用山西文学界的一位高级领导的讲话起首,对山西文学进行了革命式的总结,毫无新意,不长却臭,未了该君还不忘再加一句:“因此,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后赵树理写作”,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能够让作家、评论家、文学组织者接受的。”也就是说,为他们自己给山西文学命名的《后赵树理写作》的概念作了定论。我们姑且不说这个定论是否准确,我们只想问一句,凭什么就你一句话,就可以断定
“也是能够让作家、评论家、文学组织者接受的”?在这个口号式的“后赵树理写作“垃圾理论上站起来的作家或者作品,除了政治和概念化的奴才外,基本断定了赵树理写作是山西几十年文学创作史上一个最失败、最丢人的、模式化的悲哀。把文学创作生拉硬扯地与一个死亡而腐朽的躯体并存,再试图将之融合,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侵略,也是对读者精神的一种掠夺。一个政治强奸一切艺术的年代,一个农民的作家用农民的思想在特殊的年代写出一些让当今农民都看不懂的东西,而今却再次拿出来炫耀,这是什么用意?z
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评论家王春林说“后赵树理写作”这样一个说法的郑重提出,体现出的其实也正是(我们)后来者面对赵树理这样一个巨大存在,所必然表现出的期盼和焦虑。”我不知道这为教授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的学生在不在场,但我敢肯定,他要敢站在一个公众的、脱离了他那个圈子之外的地方说这句话,将会有无数只臭鞋砸在他的脸上,直接将他置身于“飞鞋门”事件的尴尬与难堪中。B!
“从文学的本质和意义上讲,他(赵树理)的创作自始至终处于模式化和机械状态,很难接近文学本质和达到文学本身的尺度。究其深层原因,一是赵树理本身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修养,二是眼界狭窄,三是被政治所强奸。他的作品与“时代精神”是那样合拍,尤其是建国后,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代氛围下,他的创作轨迹受到各种政治“套套”的束缚,使其作品完全变成了政治教材。还有人标榜赵树理这个作家是最民族的,这更是十足的荒谬”(邢昊:《赵树理,一个模式化的悲哀》)。就是这样的一个被政治妖化了的作家,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后来者为之恐慌和焦虑?其实,就赵树理创作本身而言,他的创作文本始终被动于历史和时代,从头到尾按着政治的需要进行文字的加码,不仅远离了文学的本质,同时也沦落成了一种卑微的政治奴隶,他所反映出来的生活同人真实的内心世界是安全不一样的。ICv*
任何一种文学创作,当“形式决定内容”成为基调的时候,还有什么可能成为文学的作品?h
对赵树理文学创作的反思,是为了让我们现在明白,把当下山西的文学创作定位为“后赵树理写作”的概念化是愚蠢而徒劳的,也是十分可笑的。即使是那些被定位为“后赵树理写作”的“麦地丛书”的作家们,也不见得就都会买你们的帐。现在已经进入个性化写作的时代,文学创作者们用个性的写作方式在不断探究着自我创作之路,“百花齐放”,为什么还要非得把作家的创作强加于什么盖头上来?^
文学是自由的,写作是个性的,艺术的才是世界的!
诗人作品
云 娘(组诗)
文/祁梦君
1
你就这样静静地躺进了季节的深处
在我远行的那个夏天,云娘,惊雷震落
满天的乌云染尽了你的霞光,有泪滴落
那满坡行走的石头于残月当空离家出走
我该是握住你干枯的手掌看着这秋叶飘零的眼泪
我该是举着谁那破旧衣裳,纵身跳下
这幽深的峡谷。雁门关外,赶路的蚂蚁,累了
那架陈旧的马车从夕阳的眉角向我走来
云娘,我不想看你苍老的面纱挂上寒霜
我不想在你熟睡的秋峦洒下泪滴
即使大雪按落云头,即使冰霜埋葬了季节
我也会在孤独的石缝间寻找寞落的诗行
2
云娘,我是你的孩子,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
写着这些散落的露珠。四野空荡,危机四伏
我寻着的喜悦或者忧伤脆弱的如同沙堡
漫野而来的水啊,让我筑不起一个合心圆
我不能把心交给黎明,不能在小城任何的角落
流浪或者停留。我挽着霞光照亮了我漆黑的脸
春唇轻启,我期盼的马帮正远道而来
它们不是我的朋友却在我的心头急速闪过
心颤抖着,没有出口。我握不住的距离,你
别离不了的伤,在远海的深处滚烫如初
雪覆盖了残阳,你覆盖了我
谁用手指在我的额头写下徜徉的悲伤
挽 歌
文/祁梦君
花谢花飞,我看见了漫天飞舞的
青丝乱衫。我想知道,想知道
那黄土之下,你的秘密。想知道
你为什么变成了水,是翠绿的河岸
那些山歌,赤裸着双脚
用清泉洗涤黎明的天窗
我想知道,为什么忧郁的目光里
在你向往的那片雪域之上
清冷或者迷离的光,在飘落
如一只深海的鱼
我看不见她的眼泪
我是那忘忧河畔的百年柳絮
静静倾听着那远远传来的梵音
让我抱着你渐渐透明的身躯前行
如同珍藏在幽谷丛林的河蚌
和风一起,把你缠绕在
柔软的草地
告诉我,为什么你的歌声象平行的铁轨
执著地向着夜的深处滑落
你是一只折翅的天使,在所有人的梦里
奔跑,却再也飞不回,原来的天堂
在我经过的时候,幻化成一座
孤独的坟
阳光穿过那片林
文/祁梦君
1
我就这样看着那大片大片的阳光
慢慢吞噬那洼 孤独的清泉
一些早起的珠儿 在忧伤的草尖
跳跃。欢欣鼓舞。这是一个注定
行走的早晨,阳光穿过那片杨林
将我的世界变成一座孤岛
远处有水鸟起落。你说,那些影子
行走在春风里。阳光暖暖的
将四月的泥土 拧成下垂的沟壑
紧锁心门。梨花漂白了梦境。还有
还有那些奔逃的背影,轻轻地捧在眼前
不忍继续,将转身的刹
那泪眼朦胧
2
你说这一生的路会这样静静走过
如这黎明前我们仰望的汝河
悄悄地流淌。没有音节的日子
忧伤穿过谁的秀发,看冷冷的冰河
默默远逝,埋葬多少蹒跚的午夜
阳光穿过那片静静的林
我梦中的仙子醒了,飞扬的广袖
旋转的酒杯,我的诗歌
醉在含愁的眼波里,躺在
流伤的眸子里,睡了。
睡了睡了
……
睡了
……
3
我们再次说起死亡。再次
想起那个幽谷丛林里的木屋
还有阳光下的孩子
远离大海,我守望的地方
月光漫过荒芜的阳台,目光
在白雪封顶的江畔 追逐无边的冷漠
早已习惯了孤独相随,习惯于
心在孤冷的残月中 穿越那些颤抖的温柔
让微笑化解陈年的遗忘
4
该是回忆擦去的痕迹,斜阳西去
谁在依风诉说。终将挥别残阳
落入晨钟。梦魂深处
木鱼敲出的泪溪隐入竹林
不要在说了吧。让那晚弥天的雾瓢着。
飘着。飘着 ……飘着……
朦胧的眼波 我牵着你的手
筑起一座孤独的城
奔向大海吧。或者寂静的花园
……飞呀……
等待的晚秋飞呀。飞呀。
飞呀
看着阳光穿过那片
春色的杨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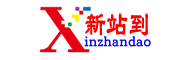 新站到阅网_Xinzhandao.COM
新站到阅网_Xinzhandao.COM

 李白介绍 李白一生总结 李白评价最高的
李白介绍 李白一生总结 李白评价最高的 当代最著名的十位诗人,全部无人不知、无人
当代最著名的十位诗人,全部无人不知、无人 燕志俊 诗人介绍
燕志俊 诗人介绍 武三思简介-武三思的诗词名句
武三思简介-武三思的诗词名句 毛依罕 诗人介绍
毛依罕 诗人介绍 建安之杰 诗人介绍
建安之杰 诗人介绍 雪漪 诗人介绍
雪漪 诗人介绍